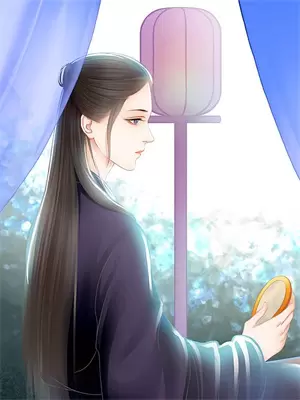
秦苏的玉笏板第三次磕到青铜鼎时,她终于听见身后传来珠帘晃动的声响。
“吉时已到——”
十二重雪缎祭服压得她肩头发沉,鎏金腰封勒得胸口发闷。香案上龙涎香混着新鲜宰杀的牲血味道直冲鼻腔,她盯着鼎身饕餮纹里凝结的血珠,忽然想起昨夜长安说的话:"明日祭典,本脉必以牝鸡司晨发难。"
“请族长诵祭文。”
左侧传来衣料摩擦声,是本脉三叔公要亲自递祭文。秦苏用余光瞥见那卷泛黄帛书,唇角勾起冷笑——果然换了文章。去年冬至那篇《女诫新解》,可是让长安在政鸾楼摔了整套青瓷茶具。
"且慢。"
清泠嗓音破开香雾,秦苏不用回头就知道是长安。玄色翟纹深衣掠过青砖,金线绣的百鸟朝凤图在晨光中泛起涟漪。她看着那双执掌政鸾楼的手捧起鎏金木匣,指甲盖上还沾着昨夜对账时的朱砂。
"祭祖大典,当以始祖手书为尊。"长安指尖轻扣匣上鸾鸟锁,"汉熙元年血誓卷轴在此。"
鼎中香灰突然爆出火星。秦苏看见三叔公的翡翠扳指磕在青铜鼎耳上,那卷偷换的祭文正在他袖中慢慢蜷曲。长安已经展开泛着褐斑的羊皮卷,念出那句她从小熟记的话:“凡我秦氏子孙,勿论男女,唯贤是用。”
"荒唐!"本脉七叔突然掷碎茶盏,"女子执政五年,族中男丁凋零,商铺亏损..."他猛地顿住,因为辞漓阁士秦妩殇的银链算盘已经甩到他面前,二十三枚玉珠将碎瓷片扫入香炉。
"七叔慎言。"执掌肃察台的女子拨动算珠,"上月本脉私卖军械至漠北的账本,此刻正在刑狱宫二宫怀里。"她身后抱着玄猫的秦晓眠适时抬头,小猫爪子里还勾着半截染血的认罪书。
秦苏忽然想笑。这些老头子永远学不会,如今鸾凤阁十二席中,有七位是能用蔻丹染指节、发簪藏密信的娘子军。她故意用折扇轻敲掌心:“既然诸位对观政考念念不忘...”
"传令。"长安的声音与檐角铜铃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