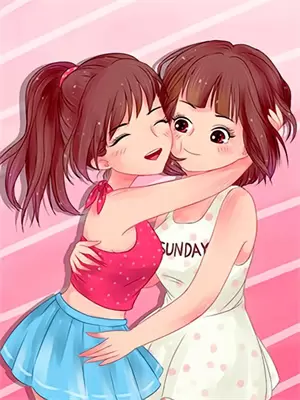
韩江精选短篇
作者: 一夜猫言情小说连载
言情小说《韩江精选短篇》是作者“一夜猫”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北狄周野两位主角之间虐恋情深的爱情故事值得细细品主要讲述的是:雪粒子扑在铁甲上发出细碎的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尝到铁锈味的血腥北狄人的狼头旗在五里外的雪丘上猎猎作像团凝固的血将粮道断了七副将周野掀开帐帘时带进一阵雪他肩甲上的冰碴簌簌往下北狄人把咱们埋在雪里的豆饼全刨走我摩挲着舆图边沿的裂那是三日前被北狄斥候的流矢射穿青铜灯台在羊皮纸上投下摇晃的光照见寒江关外七道雪沟的走势——那里本该藏着我们最后三百石粮草...
雪粒子扑在铁甲上发出细碎的响,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尝到铁锈味的血腥气。
北狄人的狼头旗在五里外的雪丘上猎猎作响,像团凝固的血渍。"将军,粮道断了七日。
"副将周野掀开帐帘时带进一阵雪雾,他肩甲上的冰碴簌簌往下掉,
"北狄人把咱们埋在雪里的豆饼全刨走了。"我摩挲着舆图边沿的裂口,
那是三日前被北狄斥候的流矢射穿的。青铜灯台在羊皮纸上投下摇晃的光晕,
照见寒江关外七道雪沟的走势——那里本该藏着我们最后三百石粮草。
帐外突然传来战马嘶鸣,紧接着是重物坠地的闷响。我抓起青玉剑冲出去时,
正看到第三匹战马口吐白沫倒在雪地里。马腹干瘪得像被掏空的皮囊,鬃毛上结满冰凌。
"还剩多少活马?""能跑动的...不到五百。
"周野的喉结动了动:"木匠老赵说...说至少要两百根横梁。"他踢开脚边结冰的马粪,
"昨夜拆了七顶营帐,弩机队的王五抱着拆下的木架哭——那是他爹传的柘木弓胎。
"我望向马厩方向,十五个辎重兵正在雪地里刨坑。
冻土下埋着三百具北狄重骑的尸首——他们锁子甲的环扣,此刻正被熔成雪橇钉。
我望着天际翻涌的铅云,想起离京那日昭阳站在城楼上抛下的绢帕。
绢帕上的褐斑突然刺眼起来。十二岁冬夜,我翻进宫墙寻昭阳,正撞见她往药碗里抖砒霜霜。
"乳娘烧糊涂了会说胡话。"她攥着青瓷勺的手紧了紧,"户部刘主事今早告病,
父皇说他喉咙里长了毒疮。"窗柩外传来重物落井的闷响,她用这帕子包住滚烫的药罐,
绣线的焦糊味混着井里泛上的血腥气,熏得她三日没咽下饭食。她说待我封侯拜将之日,
要我凭军功娶她。那方绢帕被风卷着掠过朱雀门箭楼时,
我瞥见城下民夫正往运河里倾倒砂石。三日前兵部急报说运河决堤,
冲毁了沈家祖坟的碑林——而先帝朱批的《漕运疏》还压在我案头,
泛黄的纸页上写着"嘉和六年悉征民夫二十万,沈氏茔地阻河道者,夷平"。
河道总督那夜醉酒后的话突然在耳边炸响:"你以为皇上真在乎北狄?他寝殿暗格里锁着的,
是河西金矿十二年的账本!"回过神来,我跟周野说:"把马都宰了。""将军?
"周野的瞳孔猛地收缩,"没了战马,我们怎么冲过雪原...""北狄人既敢断粮道,
今夜必有劫营。"我扯下冻硬的护腕扔进火堆。炊事营抬来第三匹死马时,
火头军老吴的刀突然顿了。他盯着马腹的烙印,那是他养了七年的战马踏雪。"将军!
这匹...这匹昨夜还驮着伤兵..."我接过他手里的剔骨刀,
当众削下自己左臂护甲:"今日沈某与将士分食同袍。"滚烫的马血溅在雪地上时,
十七个藏肉的庖丁被拖出队列,他们怀里冻硬的马腿还系着阵亡士兵的铭牌。
青玉剑映着跳动的火焰,我下令道:"传令全军,马肉分食后各营在雪沟两侧埋伏,
每人备三支火把。"子时刚过,北风卷着雪粒灌进衣领。我趴在第三道雪沟的冰棱后,
看着远处飘来的点点绿光——那是北狄人给战马绑的磷火。
"三百...五百..."周野伏在我左侧数着,喉结上下滚动,"起码来了八千轻骑。
"磷火忽然在百丈外停住,北狄阵中响起号角。我握紧剑柄,青玉剑的云纹硌得掌心生疼。
这柄传了七代的宝剑本该悬在宗祠,此刻却要饮尽胡虏血。
"呜——"狼嚎般的战吼撕破夜幕,北狄骑兵如黑潮涌来。冲在最前的赤膊大汉挥舞弯刀,
刀背上串着的铜环叮当作响,那是他们斩首的计数。"举火!
"八百支火把同时在七道雪沟两侧燃起,照得雪原亮如白昼。
冲锋的北狄战马突然惊惶嘶鸣——昨夜我们泼在雪地上的马血,
此刻在火光照耀下泛着诡异的幽蓝。"放滚木!
"埋在第一道雪沟的松木裹着冻硬的油脂轰然滚落,这是用最后半桶灯油混着马骨熬的。
周野昨日带人凿开冰河,捞出沉底的三十车松脂——那本是用来粘合箭羽的存货。
北狄前锋在火墙前急勒缰绳,战马却踏碎冰层陷入雪坑。昨夜辎重营顶着暴风雪挖的陷马洞,
此刻正吞吐着断裂的马腿。第二波骑兵刚要迂回,
雪地里突然暴起三百长枪手——他们披着冻硬的羊皮匍匐整夜,
枪头是用拆毁的粮车铁皮磨的。北狄前锋瞬间人仰马翻。
我望着那个赤膊大汉被火舌舔舐成火球,他腕上的铜环在雪地里叮叮当当滚出老远。
"第二队,放箭!"浸过松脂的火箭穿透雪幕,精准射向第二波骑兵。
那些磷火装饰成了催命符,中箭的战马带着火团在敌阵中横冲直撞。
焦糊味混着血腥气扑面而来,我舔了舔嘴角的雪水,咸得发苦。"将军神机妙算!
"周野正要跃起,被我死死按住肩甲。第三波北狄骑兵突然变阵,
他们竟将同伴的尸体垒成肉墙,推着往前移动。"果然来了。"我攥了把雪擦剑,
青玉剑锋割开雪团,露出底下漆黑的玄铁——这是父亲临刑前夜,
亲手折断又用战甲铁片重铸的剑身。当肉墙推进到三十丈时,我吹响鹰骨哨。
埋伏在雪丘后的重甲兵突然现身,他们推着的不是冲车,
而是三百架绑满尖刺的雪橇——这是用拆毁的营帐木梁赶制的。雪橇借着斜坡疾冲而下,
北狄人的肉墙瞬间土崩瓦解。我挥剑跃出雪沟时,青玉剑终于尝到新鲜的血肉。
剑锋划过咽喉的触感像切开冻梨,温热的血溅在雪地上,开出一串红梅。"沈砚!
"暴喝从斜刺里传来,北狄主将的鎏金弯刀劈向我面门。我侧身用剑鞘格挡,虎口震得发麻。
这是个满脸刺青的独眼龙,他甲胄上镶着的不是护心镜,而是用天灵盖磨成的骨片。
剑柄突然烫得握不住,恍惚间瞥见剑身似映出父亲在说:"玉可碎不可改其白,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这是连熬三夜后的幻觉。我狠咬舌尖,逼自己清醒,
独眼龙的第二刀砍来时,我故意露出左肩破绽。在他弯刀卡进肩甲的瞬间,
青玉剑穿透骨片甲胄的缝隙,精准挑断他的心脉。
"你们中原人...使诈..."独眼龙跪倒在雪地里,瞳孔逐渐涣散。
我拔出插在他心口的剑,带出一串血珠:"这招叫围尸打援。"当朝阳染红雪原时,
幸存的北狄骑兵开始溃逃。周野拎着北狄王头颅跑来时,
我正望着剑身上的血痕出神——青玉剑的裂纹里渗进血丝,像极了那年昭阳摔碎的青玉盏。
"将军!寒江关..."他的欢呼戛然而止。我顺着他的目光回头,
看见关城上飘扬的玄色军旗正在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是明黄色的龙旗。
传旨太监尖利的嗓音刺破朔风:"镇北将军沈砚接旨——"三十万将士齐刷刷跪在雪地里,
我却盯着太监手中的鎏金匣子。那本该装着封爵诏书的匣子,此刻正往下滴着粘稠的液体,
落在雪地上像一滩滩淤血。太监染血的鎏金匣子咔哒弹开时,雪地上响起细碎的冰裂声。
明黄绢帛上八个血字刺得我眼眶生疼:"即刻班师,不得有误"。"监军张公公呢?
"我攥着圣旨的手暴起青筋。传旨小太监扑通跪倒,
三日前暴毙在关内驿馆..."周野突然拔刀架在太监颈间:"你们把将军的捷报扣了七天!
"刀锋割破油皮,血珠顺着明黄衣领往下淌。我按住他手腕,
盯着圣旨边缘的暗纹——那是御用金箔才有的蟒鳞纹。"即刻拔营,骑兵营随我先行,
七日内务必快马回到京都"我将圣旨扔进火堆,火舌瞬间吞没半边龙纹。
青玉剑归鞘时发出清越龙吟,剑穗上褪色的杏色丝绦在风雪中翻飞,像只垂死的蝶。
马蹄踏碎朱雀街的薄冰时,我数着宫墙上的箭孔。十二年前太子就是在这里被乱箭射成筛子,
如今青砖缝里好像还嵌着半截断箭,箭羽上凝着洗不净的黑。
"请将军卸甲——"宫门侍卫长横戟拦住周野。我摘下头盔,发间融化的雪水流进战甲领口,
蛰得旧伤隐隐作痛。昭阳送的金创药还剩半瓶,在腰封里硌着肋骨。
金銮殿的蟠龙柱上缠着猩红纱幔,我盯着那些随风飘荡的红绸,
恍惚间又看见寒江关外被血浸透的雪。礼乐声从丹陛传来时,
我数到第九根柱子上有剑痕——那是十二年前太子逼宫时留下的。
"镇北将军到——"唱礼太监的尾音拖得老长,八千铁甲被拦在午门外。周野按住腰间佩刀,
我摇摇头,青霜剑鞘磕在白玉阶上发出闷响。穿过仪门时,
我注意到御道两侧的商贩比离京时少了七成,当铺门前排着穿绸衣的官眷。
"陛下在麟德殿设宴。"引路的小太监脖颈细得像芦苇杆,他手里提的琉璃灯罩着明黄绉纱,
照见沿途禁军铁甲上陌生的狼头纹——这是河西节度使的私兵。酒气混着龙涎香扑面而来时,
我听见珠帘后瓷器碎裂的脆响。十二扇紫檀屏风上绘着西域献宝图,
图里昆仑奴捧着的夜明珠,此刻正滚到我战靴前。"爱卿平身。
"皇帝的声音比三年前更沙哑,像钝刀磨过青石板。我抬头时,
瞥见他龙袍下露出半截玄色箭袖——这是先帝时期羽林卫的装束。昭阳从屏风后转出来,
石榴裙扫过满地碎瓷。她发间金步摇缀着的珍珠足有鸽卵大,却不及眼角那颗泪痣鲜亮。
"沈将军好威风,"她指尖绕着赤金璎珞,"听说你在北疆吃马肉?
"满殿朱紫公卿突然噤声,我望着她裙裾上绣的金凤,
想起离京那日她踮脚给我系上的平安符。符纸里裹着的不是佛经,而是她剪下的一缕青丝。
"臣请陛下赐婚。"我解下腰间玉带,虎符碰撞声惊飞檐下宿鸟。
十二道兵符在御案上排开时,户部尚书打翻了酒盏——其中三道本该在三个月前就缴还兵部。
皇帝摩挲着翡翠扳指,忽然剧烈咳嗽起来。昭阳拍着他后背笑道:"父皇您瞧,
沈将军还记着儿时过家家的玩笑呢。"她腕上缠着的鲛绡突然松开,露出半截狰狞疤痕,
"本宫去年重阳坠马时就想明白了,凤凰岂能落在草窝里?"我盯着她手腕旧伤,
想起北狄俘虏交代的情报。去年九月,确实有批镌着内府印记的玄铁流入黑市,
后来全打造成了北狄重骑兵的锁子甲。"昭阳不得胡闹。"皇帝终于止住咳嗽,
浑浊的眼珠转向我,"沈卿想要什么赏赐?"殿外忽起狂风,吹得琉璃灯乱晃。
我望着昭阳发间晃动的东珠,那本该镶嵌在她凤冠上的宝物,此刻却映得她面容模糊如鬼魅。
"臣求娶...""本宫宁可嫁给御马监的阉人!"昭阳突然抓起酒壶砸来,
西域葡萄酒泼在我铁甲上,蜿蜒如血痕。
她染着蔻丹的指尖点向我鼻尖:"你爹当年贪墨三十万两军饷,先帝仁慈才赐他白绫,
如今你也配...""啪!"翡翠扳指砸在昭阳脚边,皇帝颤巍巍起身:"来人!
送公主回宫!"但两名禁军统领站着没动,他们的佩刀柄上缠着河西军特有的犀角皮。
我捡起滚到脚边的酒壶,青铜壶身还带着余温。
壶底阴刻着"永昌"二字——这是三年前户部为修缮皇陵特制的器皿,
但去年兵部请求更换边军冬衣的奏折,批红正是"永昌库银不宜轻动"。"陛下圣明。
"我重重叩首,额头触到冰凉的金砖,"臣愿用所有军功,换先父案卷重审。
"死寂中忽然响起瓷器碰撞声,工部尚书在给御史大夫斟酒。酒液落入越窑青瓷的脆响里,
我听见至少七人调整了呼吸频率——这殿内想让我死的人,比北狄大帐还多。"准奏。
"皇帝抬手时,龙袍袖口滑出半页黄麻纸。当值的秉笔太监抖如筛糠,
因为那纸角沾着暗红印泥——是半个月前才启用的凤阳府官印。我接过赐婚圣旨时,
指尖擦过织金云纹。本该冰凉的绸面竟带着余温,像是刚从某人怀中取出。
昭阳突然嗤笑出声,她腕间的翡翠镯子磕在龙椅扶手上,碎玉崩落处露出暗格,
里头躺着柄镶满东珠的匕首。戌时三刻,我在朱雀门验鱼符。守将的铜符突然脱手坠地,
滚到青玉砖缝卡住——那缝隙里填着新鲜的血痂。周野弯腰去捡时,
低声说:"凤阳八卫今早换了防。"更鼓声掠过重檐,我盯着新赐的将军府匾额。
金漆未干的"忠勇"二字往下淌着汁水,像两道血泪。管家举着的灯笼忽然爆开灯花,
火光中可见房梁上有三道新鲜擦痕——是弩机固定架的印记。"将军,
酒窖里..."老管家喉结滚动,"御赐的三十坛梨花白,封泥全裂了。
"我拎起酒坛对着月光,琥珀色酒液里沉着絮状物。食指蘸酒在石阶上写画,
周野倒吸冷气——我描的是北狄巫医惯用的蝮蛇纹。子时的梆子声漏过第三响时,
我数到屋顶瓦片有三次不规律的震动。周野在暗处比了个手势,意思是东南角埋伏着十二人。
"将军,醒酒汤。"驿丞端着漆盘的手很稳,但托盘边缘有新鲜抓痕。我端起青瓷碗时,
看见他中指甲缝里藏着朱砂——这是御药房配鹤顶红时用来标记的。汤药泼向房梁的瞬间,
三支弩箭洞穿窗纸。我翻身滚到屏风后,听见门外传来人体倒地的闷响。周野的刀很快,
但第一个刺客的惨叫声还是划破了夜空。"换岗时间。"我扯下帘幕裹住剑锋,
青霜剑穿透木窗时,正好刺中第二个弩手的喉结。温热血珠溅在窗棂上,
映着月光像一串珊瑚珠。当第六具尸体倒下时,活着的刺客突然咬碎毒囊。我掰开一人的嘴,
看见后槽牙镶着金箔——这是内务府死士才有的标记。周野扯开刺客衣襟,
露出心口靛青刺青:盘龙纹里藏着"羽"字。"羽林卫旧部。"我用剑尖挑起刺客衣服,
"但这些人是骑兵。"我掰开刺客僵硬的脚掌,厚茧里嵌着暗红砂粒。
周野突然扯开自己战袍,左肋箭伤疤下藏着块油布:"去年驰援凤阳关,
我在关外二十里陷过马。"油布里裹着的正是同款朱砂土,混着几粒金砂。
而河西军今冬新换的棉衣内衬,
此刻正簌簌落着同样的金粉——这是熔炼金矿时才会有的碎渣。更夫第五次敲梆时,
我们站在城西义庄里。仵作举着油灯的手在抖,
灯影照见停尸板上熟悉的箭伤——这些尸体的铠甲夹层里,缝着河西军特供的驼绒。
"将军你看这个。"周野撬开死者口腔,镊子夹出半片金叶子。我对着月光转动金叶,
边缘细小的齿痕突然与记忆重合——去年截获的北狄密信上,也留着同样的压痕。











